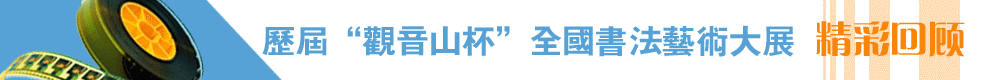林散之(1898-1989),原名以霖,别署左耳、散耳,晚号聋叟。早年曾名“三痴”,取痴迷诗、书、画之意,散之即为“三痴”的谐音。原籍安徽和县乌江。历任安徽省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文代会委员。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、江苏分会名誉主席、江苏国画院画师、南京书画院院长等职。
林散之出生在当时的一个小康之家。但在14岁的时候,父亲早逝,家道骤落。迫于生计,经父友推荐,到南京随张青甫画工笔人物,从此走上了学艺的道路。不久返回乌江,从乡亲范培开学习书法。范授以唐碑和包安吴的执笔悬腕之法。弱冠后,又从张栗庵学诗古文辞。张栗庵是前清进士,藏书甚富,学贯古今,书学晋唐,于褚遂良、米海岳尤精。30岁前的林散之在张的指导下,诗文书画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更因为张的大力举荐,林散之又得以结识了国画大师黄宾虹。黄宾虹感其学艺的真诚,非常赏识,说:“君之书画,略具才气,不入时畦,惟用笔用墨之法,尚无所知,似从珂罗版摹拟而成,模糊凄迷,真意全亏。”接着又示之用笔用墨之道。又曰:“君之书法,实处多,虚处少,黑处见力量,白处欠功夫。”(见《林散之书法选集·自序》)闻听此言后的林散之大为惊骇,“遂归江上闭门潜学……痛改前非,不辞昼夜,惟积习既深,改之不易,竭三年之力,稍稍变其旧貌”(见《江上诗存·自序》)。
在黄宾虹那里,林散之不仅明白了艺理,观摩到了唐宋以来大量的古碑佳帖,眼界日益开阔,理解愈加深刻,而且他受到黄宾虹以造化为师的治学方法的影响。黄曾对他说:“凡病可医,惟俗病难医。医治有道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”(见《林散之书法选集·自序》)林散之于是萌发了远游写生之念,挟一册一囊,从乌江出发,只身作万里远游。凡经河南、陕西、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,又转安徽之九华山及黄山而归,计跋涉一万八千余里,得画稿八百多幅,诗二百多首,游记若干篇。书画之艺,自是大进。
60岁以前的林散之,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乡间。解放后,林曾任江浦县副县长,修田治水,以书画为余事。65岁那年,他正式调入江苏省国画院任专业画师,从此得以潜心艺事。那时他的画名比书名重。1972年8月,为庆祝中日恢复邦交,《人民中国》杂志社编辑出版“中国现代书法作品选”特辑,由田原等人推荐,经赵朴初、启功、郭沫若等人肯定,将其作品列于首位,方才声名大噪,这时的林散之已是70高龄了。
林散之的书法,初从范培开得以入门;又从张栗庵奠定了书画和古文诗词的基础;从师黄宾虹,使他步入了艺术的堂奥。而1972年“中国现代书法选”特辑的出版问世,则奠定了他在当代书坛的地位,从一名沉埋于僻乡的民间艺术家,一跃成为轰动全国的名家。50年代以前的林散之以山水画的创作为主。他的山水师法黄宾虹,力追南宋,喜画重峦叠嶂,笔墨淋漓。50年代后始专注于书法。70岁以后,书名掩其画名,又以作书为主。
和每一位有成就的书家一样,林散之在传统上下了很深的功夫。由唐入魏,由魏入汉,转而又入唐宋,降及明清,皆所摹习。汉之《礼器》、《张迁》、《孔宙》、《衡方》、《乙瑛》、《曹全》,魏之《张猛龙》、《贾使君》、《爨龙颜》、《爨宝子》、《嵩高灵庙》、《张黑女》、《崔敬邕》,晋之阁帖,唐之颜柳、李北海,五代之杨少师,宋之米元章,元之赵文敏,明之王觉斯、董思白诸公,均力学之。
从他师法的碑帖和家数来看,林散之是不计较碑帖的差别的。相比于那些尊碑抑帖或扬帖抑碑,固执一见的书家,林的多角度、全方位的撷取,保证了他日后将不会在某家某派里面讨饭吃,而是极早地为其书法宽厚的包容和涵纳能力做好了铺垫。
和当代另一位书法名家沙孟海的临作相比,沙重视形神兼备和功底的扎实与否。而林的临作可以看出是属于那种重意不重形的一种。这和他接受过黄宾虹的教诲有关系。黄曾说:“书画之道,应以笔墨为主,无笔无墨,何以成画?古人千言万语不离其宗,口传心授,自有真诠。君宜静心观察其运用玄旨,重在参悟。”(见《江上诗存·自序》)基于这样的观点,林在临摹中始终是注重一种感觉上的把握,而不以形态的惟妙惟肖为目的。以个人的好尚趣味为中心,有意识地对那些风格不一的碑帖加以选择和理解式的临摹,是他的一大特色。他服膺李北海,自言于北海学之最久,在40年代的临作中,点画的使转实在是过于生硬,但李北海的奇支侧生姿的意味把握得很有分寸。与此相似的《临颜真卿书李玄靖碑》,取秀润丰满,舍庙堂之气。70年代临写的大量汉碑,无论粗重古拙,皆以雅逸清健的笔调摹习。从临作中,看不出他对传统有多么厚的继承功底。但恰恰相反,在他的创作中,却体现了他的学有渊源和非常明显的个人审美倾向。
林散之自言16岁开始学唐碑;30岁以后学行书,以米为主;60岁以后学草书。纵览他平生大量的作品,基本上如同其自言的格局。书于1921年的《诗抄》和1927年的《山水类编序目》,显示了他青年时期在楷书上所取得的成就。端庄小楷,法度谨严,是唐人的特色,而清峻古雅、不染尘俗,却没有一般从唐楷入手而带来的刻板、局促之气。本世纪作唐楷的人,不计其数,若以格高韵足而论,达此境界者,绝无仅有。即使将之与文、祝二家的小楷书置于一处,也毫不逊色。林在楷书上是下了苦功的。没有这样的底子,也便没有晚年草书出神入化的可能。30岁以后的行书,的确有一番爽快的趣味,但又不全似老米的风樯阵马式的痛快淋漓,而是从容镇静,有了一种悠闲和自得。60年代,他的草书开始有了飞跃式的发展。“以大王为宗,释怀素为体,王觉斯为友,董思白、祝希哲为宾。”(见《林散之书法选集·自序》)寒灯夜雨,汲汲穷年,经过数十年的艰苦磨炼,他终于在草书里寻找到了最适宜于表达抒发自家性情的书写语言。之后的二十余年,林致力于草书创作,惨淡经营,力图革新。80岁前后为一分界线,之后,草书的风格又一大变。从奔放洒脱的意气风发过渡到老辣古拙和平淡天成的境界,所谓的人书俱老,即是如此。
在诸体书中,林最擅草书。林散之被世人誉为“当代草圣”与其所擅书体不无关系。他的隶书次之,多飘逸舒展。书于1963年的自作诗扇面《罗江》,一反常态,奇崛高古,不假修饰,反映了他在书学审美上的多向选择。他的楷、篆书作品不多,偶而为之,不甚用心,但多有趣味,是其草书的辅助,无论篆隶楷行草,他的笔调基本是一致的,静谧雅逸的氛围贯穿其终生的作品之中。
若说林散之早、中、晚三个阶段书法面貌的变化,那就是线条上的锤炼日益娴熟。从师黄宾虹后的最大收益,是他以此树立起强烈的线条至上的意识。林对线条的特别关注,是在60年代。书于1962年的毛泽东词《采桑子·重阳》和书于1976年的自作诗《太湖记游之一》可看作是所谓的锥画沙、折钗股、印印泥、屋漏痕、壁坼纹的形象化的体现。古人的形象比喻,无非力图说明线条的质感和力度以及其中立体的空间感觉。这件作品线条瘦硬,缠绕连绵,圆劲遒媚,润涩相济,纤纤细线,在纸上所留下的虚实相生的笔道,如同千钧之力的刻划,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这种令人惊讶的瘦细柔韧的线条,在古人的作品里,还从未有过。张旭擅长狂草,线条受到唐代时风的影响,略显丰肥;怀素线条较细,中锋用笔,笔力内涵,也不见其瘦。后来的黄庭坚、祝允明、董其昌、王铎诸家,均不曾做如此险绝的尝试。林散之手中的那支特制的长锋羊毫笔,使他的线条拥有了足够的弹性和丰富变化的可能性。古人常用的短小硬毫,远远不如这种长锋柔毫更具有表现力。林善用此种毛笔,“拖泥带水”,翻转起偃,若纵若擒,举重若轻,极尽变化之能事。晚年的作品,常以浓墨涂抹,1984年写的自作诗《小阁》,迟涩行笔,斑斑点点,濡墨处,如同漆块,渴笔处,一片云烟。远望长卷,苍苍茫茫,一片虚灵,如同梦幻一般。
林散之的作品中,线条是第一位的,结构则在其次。在很多作品里,有些字的结构处理并不美,甚至松垮散漫,无意求工。他的注意力都在线条的挥洒上,作品的连贯、完整均靠一以贯之的线条统一。有时,他太着迷于那些超长线条的纵意宣泄,往往形成了一种长蛇挂树一般的形象,极不和谐。在线条的细微处,精彩之极,通篇的作品又常常因其结字的松散和长尾的拖沓,难以令人赏心悦目。这是林散之书法的一大弊病。
不管怎样说,林散之在书法线条上的锤炼在本世纪的草书家里,是无人望其项背的。把他的线条与历代草书大家作一比较,也是非常出色的。林终生孜孜石乞石乞,潜心书艺,他的理论很少,他的影响和魅力主要来自于那种精灵般变化无常的线条。这种线条意识在他的晚年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是林散之不曾想到的。早年他就有些耳聋,晚年与人交流,只能笔谈,加以年迈,足不出户,一片宁静之中,专注于线条的塑造,外面喧嚣的书坛他几乎无动于衷。在建国后的数十年里,由于书法艺术观念上的滞后和书法教育的普及性局限,从一些著名的书家到初学者,大多数都在斤斤计较着结字平正均匀的美观和实用上,对于线条的重视远远不够,甚至极为淡漠。而林散之强烈的线条意识,在新时期书法到来后,随着人们艺术观念的解放和对书法本质认识上的提高,愈来愈受到重视。可以说,林散之的线条形式,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现代书家对线条的特别关注。这也恰恰证明了他笔下的线条魅力无穷。
林散之是一位沉迷于山水的画家。在他早年的书法作品里,由于还比较顾及传统笔法的运用,除了不落俗套的气味外,无甚可取之处。50年代后,他的精力开始转移到书法创作,并把山水画的水墨形式语言、皴擦技法和构图法则等运用进来,丰富了传统笔法,拓展了线条的表现力度,增强了章法布局上的黑白虚实的对比,渗入了具有鲜明时代感的现代空间意识。
首先是水墨的运用。其师黄宾虹曾经谈到的七种用墨法,在林散之的作品里,运用较多的是浓墨、淡墨和渴墨。书画虽然同源,但毕竟各有特色,混为一谈,非书非画,不算成功。相比于国画,书法中的墨色变化,历来比较单一。明代的董其昌,喜用淡墨,明清之际的王铎,常用“涨墨法”,可以说是水墨在书法线条运用中较早的尝试。但上述二家的试验都未脱离传统笔法基本的要求,而有意识地最大限度地运用水墨技法的,要属林散之了。在他成熟的草书作品里,渴墨与浓墨、淡墨常常是联系在一起应用的。由于长锋羊毫的蓄墨量较大,林在一些长条幅作品里,多饱蘸浓墨,一拓直下,中途不作停顿,直到笔中的墨倾泻干净为止。所以作品中黑白虚实的对比异常强烈。林散之用浓墨长于淡墨,因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非凡的驾驭毛笔的能力,用浓墨书写的作品尤见笔力。而淡墨就不同了。书法中如过多地或不加控制地运用淡墨,极容易形成一些臃肿不堪的墨块,有墨无骨,失去了书法线条的基本存在形态。林在70年代以后,曾长期探索以淡墨作书。水墨运用恰到好处时,的确增加了一些空灵之气;运用不当时,也常常是一塌糊涂。大多数的淡墨作品都给人一种丰肥滞泥的感觉。林散之不是那种功底型的书家,他常凭灵性作书,和水墨无常的变化一样,或神采飞动,或败笔迭出。书于1974年的《许瑶论怀素草书诗》中的“古瘦漓骊半无墨”数字,书于1984年的“山花春世界;云水小神仙”,上下联的最末两字,均有精彩动人的意外表现,水墨交融,渗化洇散,禾农纤适度,枯湿合宜,有书的形质,画的意境,大大弥补了作品整体上的丑陋。书于1977年的自作诗《论书绝句》:“笔从曲处还求直,意到圆时更觉方,此语我曾不自吝,搅翻池水便钟王。”可以算作是他运用水墨作书最为成功的一件作品。通篇一气呵成,几无懈笔,或水墨氤氲,或干擦涂抹,或蹲锋绞翻,或擒纵跳跃,充分发挥了水和墨各自的特性,润而不腻,丰而不肥。可惜这样的好作品太少了。
其次是皴擦等绘画技法的应用。皴法在山水画中有多种,用笔多侧卧为之。这和书法中传统的用笔法是有差别的。80年代后林散之创作的众多作品中大量参用了皴法,书于1983年的《王昌龄送辛渐》,渴笔纵横涂抹,那意味抽象的笔墨,与山水画中嶙峋的丑石别无二致。在绘画上,以书入画早在两宋以前,即已开始。明代的董其昌,深通中国书画的堂奥,更加重视绘画中笔墨表现的效能。由于董其昌的大力开拓,致使清初的石奚谷与敏悟“画法关通书法津”的石涛均走上了既穷丘壑之变又穷笔墨之变的道路,丘壑师造化,笔墨也师造化,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。以画入书的林散之,仍然保留了传统用笔法的诸多基本要求,只是完成的过程和手段有所不同,但线条的存在还是一个事实,无论它变得多么扑朔迷离,几欲使人看不透笔锋来来去去的踪迹。
林散之成熟的草书作品,在章法布局上,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格模式。受王铎大草书的影响,气势连贯,笔意流畅,纵横挥洒,一气呵成。1972年书写的《自作诗二首》,随着柔美线条有节奏的提按,犹如一段舒缓轻柔的曲子,忽而沉重,忽而倾吐,缠绵悱恻,韵味十足。书于1978年的《太白楼放歌》,节奏感大为增强,诗中豪迈的情性通过笔墨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,行与行相对独立,字与字则紧密相联,字形多以直线和曲线组成,柔中有刚,顿挫分明。这种古典式的作品并不太多,更多的是融以画理之后的作品:大疏大密,黑白错综,实处见虚,一扫前人平板的布局,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刺激。
林散之书法成就的取得,是善于继承古人的结果,是创造性地借鉴绘画技法的结果,更是他耻于步人后尘,勇于变异的结果。
他在自作诗中说:“独能画我胸中竹,岂肯随人脚后尘。既学古人又变古,天机流露出精神。”“以字为字本书奴,脱去町畦可论书。流水落花风送雨,天机流出即功夫。”他不满足于个人的成就,不愿做继承上的名家,他要有自己的面目,要不同古人。在他长达80年的艺术生涯中,书风四次大变。即使手残以后,仍作书不辍,在《临熹平残石》后面题到:“伏案惊心六十秋,未能名世竟残休。情犹不死手中笔,三指悬钩尚苦求。”这种勇于否定自己,不断探索,“书”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,反映了一名艺术家真诚地献身于艺术的可贵品质。
相关文章
- 薛元明:笔法杂谈2014-08-13
- 薛元明:谈结字2014-08-13
- 名家谈国展创作——陈海良2014-08-08
- 名家谈国展创作——汪永江2014-08-08
- 名家谈国展创作——张建会2014-08-08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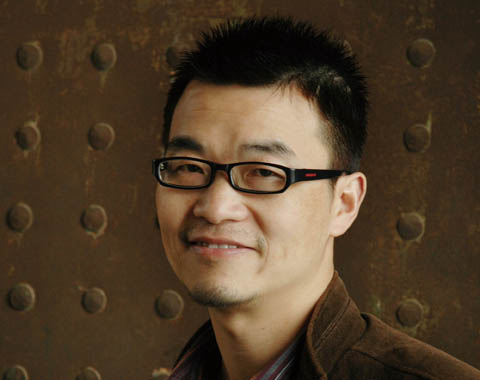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
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
以文泉于楷书勤苦之根基,其行草研习可谓平川走马,纵
-
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
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
张华的篆书与篆刻都是小写意风格,他准确地把握每个字
-
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
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
书学通心学,阳明讲“心即是理”,伯安又言“心外无物
- 陈鹏酒后戏作《将进酒》(上)
- 10月13日夜,老鹏做客择一堂,酒后戏作草书《将进酒》8条屏,有幸得孙辉兄拉纸,王伟平兄、杨圣山兄拍摄。...[查看全文]